|
我竟然梦见了这些事。首先我梦到了他。他在哪里?他在梦里。我不是说我梦见他时,他在我的梦里,这不是废话吗?我是说,我刚梦到他时,他也在做梦。也不是这样,越说越糟。我是说,我梦到他在做梦,而且梦到了他的梦。我梦见一个硕大的石榴,有地球那么大,裂开了许多口子,我从其中一道裂缝钻了进去。于是,来到一大片珍珠中间。这些珍珠密密匝匝,一颗紧接一颗,像空气一样柔软。我看到他在这些珍珠中间散步。在这个天地里,只有他独自一人。他用手抠下几颗珍珠,放到嘴里品尝。其实,这样描述,还是让人觉得我只是梦到了他在散步。干吗说梦到了他在做梦和梦到了他做的梦这么玄乎呢?哎呀,你们误解我了,我不是那种玩概念的人。打个比方吧,如果仅仅把梦看成画面的话,那么这幅画里的确只有他,而没有他的梦。但是我的这个梦,除了画面还有一个“脑子”。这个脑子通过分析画面,而得出结论。当时,这个梦的脑子告诉我:你梦里的这个石榴、这些珍珠还有这个人并不直接属于你的梦,它们直接属于你梦中这个人的梦;因为你梦到了他的梦,所以你间接地看到了他在你梦里散步。简单地说,我当时虽然也在做梦,但我还是很清醒,我知道我梦见了他梦见自己走在一颗石榴里。更复杂的事又开始出现了——不知是我在我梦中想,还是他在我梦中想,还是他在他梦中想,反正就是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出现在梦里:他将遇到一系列恐怖的灾难。这些灾难将降临这个石榴,出现在他面前,向他张开血盆大嘴。他怀着这种预感,忧心如焚地走在石榴里面。但是他却发现了一本小说。那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封面十分精美。那正是我的第一本书。(事实上我虽然写小说,却从来没发表过作品,更没出版过。此文中若再次出现与现实不一致的地方,恕本人不再注释。)他,作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令人难以理解地关注起我这种无名小辈的文学作品来。他十分仔细地读着,一点也看不懂——他发现这是一个中国人写的小说。这时,一个巧妙的因素切入:不是我的这个梦的脑子,而是我梦中的他的那个梦的脑子提醒了他:别紧张,这很可能是在做梦!于是他灵机一动,麻烦就迎刃而解了。也许是我小说里的文字奇怪地变成了西班牙文,或者他一下子就变得能识汉字了,反正他看懂了我的小说。他首先看了看作者的名字,“鳜膛弃……”他的嘴巴张了两下。也有可能他说的是“Great Touch”,反正发音相似。他高兴得跳了起来,为他终于能毫无阻碍地阅读这本小说而由衷地高兴,以至于情不自禁地抓了一大把珍珠塞进了嘴里。他不到一分钟就读完了它,但这不代表他敷衍了事。相反,他读得相当认真。他读到了我的那篇《画家》,很高兴我能写一写画家,但是对它的内容很不满,他认为这名作者根本就不了解画家,画家哪里是这个样子的?他很不服气,对这名作者破口大骂。(注意,他虽然是一名天才,此时甚至有一点预感到自己是在梦里,但他万万想不到他的这个梦以及他梦里的他都存在在我的梦里,更不知道我便是这本书的作者。)但是除了这篇《画家》,其他作品都令他振奋。特别是那些关于时光的形状的描述(里面提及了时光在物质意义上的变形及扭曲,时光在生物学上的表情)和关于梦的各种“场”的图像化的那些作品,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在《当时间饥饿时》这篇小说里面,有一个句子令他得到了某些启示,他马上记在了本子上,这个句子便是:“时间的面孔试图拥抱荒漠里的老树的枯枝,这老树在时间被发明之前便已矗立在此,而现在当时间疲倦地来临,它向天空露出一只手臂上的伤口……”,还有这句:“时间的一瓣屁股跌倒在一具死去的怪兽的尸体上,另一瓣屁股有着从丑陋的悬崖边滑下去的危险。”他把这两个句子念了好多遍。在《一个城市的五万居民的梦》这个短篇中,他看到的是数不清的光怪陆离的梦境,以及这五万名居民的梦之间道不尽的联系。比如,我在里面写到了,一位名叫罗大夫的侦探在梦里塑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医生,名叫弗洛伊德,他在罗大夫的梦里的生活只两件事情可做:看病和写书。他尤其写了一本关于梦的书。结果,由这个现实世界中不曾存在的人写的这本关于梦的书,却被这城市里的五万居民竞相传阅,在这本书的指引下,他们按自己的愿望做了更多美好的梦。另一名叫H的诗人看过这本书之后,大受启发,遂不再写诗,而是勤奋地做起了梦。在梦里,他也学罗大夫的榜样,像创造小说人物一样创造出一位名叫博尔赫斯的小说家。H还在梦中(对博尔赫斯的塑造他是分好几个梦完成的)把弗洛伊德的书介绍给了博尔赫斯。这样博尔赫斯便成了同弗洛伊德一样伟大的天才。这一点令H如愿以偿。虽然H也读了弗洛伊德的书,而且也足够聪明,但是要变成天才可能还需要二十年,所以他干脆做起了梦,在梦中制造了博尔赫斯,他让博尔赫斯去变成一个天才——结果只花了二十天。这个变成天才的博尔赫斯,很不屑于弗洛伊德的观点(主要是不屑于他的成就),也写出了很多关于梦的小说。都写得很传神。以至于,梦有了将要取代现实世界的倾向。H本来就对自己梦中制造的这个博尔赫斯很不满意,他原本是想让他替自己写诗,谁知写了一阵子诗之后,博尔赫斯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写那些关于梦的小说上面。而现在这些小说里的梦渐渐强大起来,H开始感到不安,他怕梦取代了现实,那样也就代表博尔赫斯取代了他。他想在梦中把博尔赫斯杀死,令他想不到的是博尔赫斯先下手为强,只用两秒钟就涂鸦了一篇叫《镜子与面具》的小说,在小说中作者让诗人被国王赐死。于是第二天,人们发现H死在自己床上——他在梦中自杀了。接下来,博尔赫斯又写了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开篇就描写了一个梦——梦里一座城市消失了。不用说,第二天,这座有着五万名喜爱做梦的居民的城市从地平线上彻底不见了,五万居民包括在梦中制造了弗洛伊德的罗大夫全被埋在了地底下。从此,关于这个城市的一切,便只剩下弗洛伊德和博尔赫斯两个人。不久博尔赫斯又写了一篇三页纸的小说,小说中,一名牧师梦到一名超现实主义画家画了一幅画,画中是一名集耶稣同犹大为一身的木匠做的一个梦,这名木匠梦到一个中国的文学爱好者在一边挨饿一边写着一篇题为《一个城市的五万居民的梦》的小说。
这篇十分精彩的小说(它一直是我的骄傲——当然也是指在梦中)使得他(本文开头的他,以下直接称他为画家)狂笑不已。正是这不可抑制的精神癫狂使得画家落下终生的疾病——狂笑症。我刚才还在梦里觉得他是一名天才画家,现在却突然看到,作为画家他根本没有画过一幅自己的作品。这句话或者这样表述:虽然他刚才还在我梦中的他的梦中觉得自己是一名天才画家(这似乎曾是一个事实),但他现在发现,作为一名画家,他根本没有画过一幅自己的作品。所幸的是,我的这本小说深深地启发了他,他毫不害臊地认为:我作品中的这些东西,其实一直装在他脑子里,或者曾在他以前的无数梦中出现过(他甚至还认为他曾几次梦到过我,我在他的梦中欣赏了他的那些关于梦的画作,所以我才能写出这些关于梦的小说)。是的,我说,其实是他梦到过我的思想,而且很多次想要借绘画表现出来,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表现手法。但现在受我的小说的影响,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灵感和信心去创作了。他非常满意,作为一名初入艺术殿堂的年轻人,他向我这样一位同样年轻而伟大的艺术家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当读到我后期的作品时,他发现我的创作兴趣发生了转变。我不再关注时间的形状和梦的深刻寓意。我的兴趣竟然转向了呆板的现实主义!我开始描写男人和女人(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字)的日常生活,连他们在厕所里的行为都写到了。这令他极为不满。他怀疑那是我老年时写的作品,或者是剽窃当代中国某些作家的作品。我在一篇极其枯燥无味的小说中写到(用的同样是乏味的现实主义手法)七个女人和一个头盖骨的故事。他看过之后,连连摇头:“这七个女人虽然给人印象深刻,有血有肉,但她们同这篇作品一样俗不可耐。”他看上去非常生气,同时又为自己敢于批评我这样一位伟大艺术家的这种勇气沾沾自喜。出于对我的尊敬,他才没把整本书扔掉。他只是将它重重地合了起来,并在一块尖尖的石头上用力拍打了几下。这时,一个头盖骨——就是我那篇失败的作品里的那个头盖骨——从我的书里面跳了出来。一开始,它化作一只老虎向画家龇开了大嘴,吓得他像一个女人一样地尖叫起来,在地上滚了几下,压坏了不少珍珠(我梦中出现了画家睡在自己的床上翻了个身,并张了张嘴的短暂画面)。正当画家爬起来,准备落荒而逃的时候,老虎又变回了头盖骨。这个头盖骨迅速膨胀,不一会儿它取代了整个石榴,吞噬了惊慌失措的画家。
画家吓得从梦中醒了过来。讲到这里,我松了一口气。因为画家终于不是在他自己的梦里了,而我也终于不用面对同时讲述两个梦的困难了。但画家仍然在我的梦里,因为我还没醒来。我得接着讲这个古怪的梦。
画家满头大汗地惊醒过来,他马上被现实中的困境吓了一跳:在这个梦之后,他觉得自己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他有太多的作品要画,那些作品现在已经全部装在了他脑子里,再清楚不过,他巴不得只用一秒钟就把它们全部画下来。准确地画出那些作品,他现在已经有了那个能力,但不是在一秒钟内,他非常清楚,要画完它们,可能将耗去他毕生的时间,因为那些作品太多、太丰富。可是,先画哪一幅呢?
他决定先向那个不祥的头盖骨开刀。那是最令他不安的东西,它装在他脑子里将会使得他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得将它移到画布上。越快越好!他想起了那个瞪眼咧嘴的玩意是在鳜膛弃的一个糟糕的小说里跳出来的,小说中同样还出现了七名叫人讨厌的女人。他决定将女人们变成头盖骨,这个想法令他感到自己的阴险,但是经过这个梦之后,他已经不再是一名善良的艺术家了。他只在乎自己的狂热和鬼点子,一切叫人惊奇的想法,和愚弄大众的艺术满足感。他想,如果一个句子的力量可以杀死一名无辜的人,那么小说家宁可上断头台也要写下这个句子。同样,如果一幅画可以在人群中炸开花,让他们血肉横飞或是魂惊魄散,那么画家也会顶着一切后果狂喜地创作这样一幅画。
他开始到大街上找第一个女人。他不能去找那些漂亮而又高贵的少妇们。那些尊贵的小姐或太太们。那些拿着夸张的扇子在博物馆的画展上用鼻子嗅着油画的侯爵夫人或子爵夫人们。教授们的女儿当然年轻,也不算很丑,而且有点艺术修养,但她们见到衣着寒碜的男人都会尖叫。最可怕的是那些聪明的女人,打着优雅的哈欠,见到画家走过来,就用讥讽的口吻问他:“你是不是刚做完一个梦啊,我的画家先生?”
“呃,是的……”可怜的画家说。
“是不是梦到了令人激动的艺术主题啊?”
“是的,可是……”
“是不是你现在需要找些漂亮女人来帮你完成你的作品啊?”
“当然,不一定要漂亮。”
于是她们发怒了。画家被女人们追赶着逃到一家妓院,因为除了这个地方,我们这些崇高的妇女哪里都敢去。画家纳闷那些女人怎么会知道他梦里的事情,他可从没有提起过。不过,他现在有了这样的想法:自从在梦中读过那本中国小说之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更没有什么可以称作怪事了。
接着他有了惊喜的发现。他看到一大排女人立在他面前。每一位都身材高挑,既不胖也不瘦,脸蛋嘛……反正脸蛋不是很重要。他真是太高兴了,因为他在妓院。这地方他还不熟悉吗,以往在创作上遇到阻碍时,他就会来这里堕落、发泄,也算是寻找灵感。而他以前根本没有画成功过一幅作品,所以他光顾此地也就特别频繁。他只要手指头一点,其中一名妓女就会跟他走。每一位他都熟悉(这使得他有时犯难,不知该照顾谁的生意),他了解她们的身世和内心,对她们充满感情。他还热心地给她们讲解艺术,但是她们听了之后(她们并不是听不懂)都抱怨:“艺术这东西很讨厌,它越来越让我感到自己的不幸了。”这反而使得画家认为她们全身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艺术细胞。
说实话(我这个梦管得太宽了!),画家之所以一开始没有想到要来妓院找模特,是因为他将创作的是那个可恶的头盖骨。那是一个让他讨厌、让他蔑视甚至仇恨的东西。它代表死亡,和不要脸。那么构成这幅画的就不应该是这些他所同情和热爱的妓女们,而是那些被他所瞧不起的浅薄和骄傲的女人。他要在她们身上揉进死神的微笑,让世人感受到她们的恶心。但是他现在没办法做到这一点了,事实证明,现在反倒是他令她们感到恶心,是他被她们所仇视。想到这,他悄悄地出现在临街的窗前,他看到那些围攻他的女人们渐渐地在无奈中不甘心地散去。他松了一口气,微笑着望向那么多他的小甜心。妓女们这时本应该站立端正,面露媚态,但是画家对她们来说实在是太熟了,熟悉得就像她们自己的丈夫,所以她们全立在那里东倒西歪,毫不掩饰地哈欠连天,有的冲他做着丑陋的鬼脸,或是挥舞着小拳头,吓唬他。
画家舒服地伸展了一下腰肢。他突然觉得很幸福。像对着自己的一大堆财产,他像个财主似地变得神气起来,挠着头皮,不怀好意地笑了笑,这就代表他要作出选择了。姑娘们故意装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虚伪神态。
这时,一个名叫艾芙艾特的姑娘跑过来,用手臂钳住了他的脖子。
“你知不知道,我昨晚梦见你了。”那小妖精说。
“梦到我?”
“在吃着一个又大又圆的苹果……”
所有姑娘都大笑起来,她们知道那句话的意思。倒是画家显得有点拘束。
“那……你肯定是苹果吗?”他强作镇定。
“也可能是石榴。反正是你们男人爱吃的……”
画家想起梦中的那些珍珠。“就你吧。你总是那么会说话。”
看到画家选择了艾芙艾特,别的姑娘一齐发出一片嘘声。“每次都是她!”有人埋怨。其实,这不是实话,画家很久没有照顾过艾芙艾特了。不过女人们喜欢夸张,更何况是在妒忌的时候。就这样,她们都变得垂头丧气。有的姑娘其实是打心底爱着画家的。
画家微笑着望着她们(他怀里搂着艾芙艾特),他的笑充满了神秘。“还有你、你……你和你。”他又一口气点了六个。
这当然给她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不过也有人为他担心:“两根毛先生,你怎么回事?你想自杀吗?”
“真的呢!你能行吗?不要勉强自己,我们可不难为你。”
“算了,我不去啦,你下次多关照我就是啦。”
画家又露出一个十分艺术的笑容,就像有人拽着他的两根胡须往上提了一下。他充满信心地说:“放心吧,我今天可是一个巨人。”
姑娘们又一次误解了他。他现在就是要故意制造这种误解,好让她们去到他的画室。
在路上,画家(七个妓女簇拥着他!)开始感到不安,所以他先暗示她们:“你们放心,我的要求很小。”
画家说出这种不符合他性格的话令姑娘们感觉蹊跷。有人尖锐地问他:“喂,流氓!你是不是想不给钱啊?”
这倒真正让画家头疼。他身上确实没多少钱了,付给七个姑娘肯定不够。
“你不是想用你的狗屎艺术来换取我们的贞操吧?”老妓女吕西说这么逗的话,害得其他姑娘的肚子都笑痛了。
但是画家却笑不出来。他在想:到哪里去弄钱呢?
他就地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流浪在犹太人聚居的城市的街头,一边行乞一边靠给路人画像挣几个钱。奇怪的是,他竟然替我小说中人物罗大夫的梦中的人物弗洛伊德画了一幅像。弗洛伊德,这位梦的专家,一眼就看穿了这位别人梦中的画家背后的故事,甚至看出了装在画家脑子里的那个头盖骨。虽然他没说什么,但我们的画家却开始紧张起来。他握笔的手开始颤抖,最后一不小心的一笔使画家在画像里准确地预言了弗洛伊德的完蛋。弗洛伊德死后,他的画像轰动了一些人,于是不多不少的钱财流向画家的身上。有了钱,画家便草草结束了这个梦。
当他从这个梦回到我的梦里时,他和七妓女已经来到了他那阴暗、局促而且乱七八糟的画室。姑娘们在七嘴八舌地聒噪。“你们在谈论什么?”
“色狼,你来评评理。”艾芙艾特说,“绿蒂这不要脸的小蹄子竟然说她比我漂亮。”
“有时候,我是比你……漂亮。”绿蒂这孩子看来比较诚实。
“你们都很漂亮。”画家说。他说得很真诚。
但有的姑娘还是不买账,因为漂亮是不够的,得比别人漂亮才行,所以她们还是争论不休。
“他妈的,别吵了!”画家现在有了钱,说话比较有底气。“开始干活!”他大声令下。
“你们谁先上吧!老娘只想好好地睡一觉。”吕西故意这样说,虽然她很想马上占有画家,但她知道:第一个永远轮不到她,别落在最后就算好事了。她是比较可怜的一个,也比较穷。
有人开始找床。可是根本没有床!“这是什么鬼地方?”那姑娘这样质问,同时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表明这个烂地方只配用来吐口水。于是,大家都发现这里原来是画室,而刚才她们因为争论着谁漂亮,一直没注意到。
“洗澡的地方也没有!”有人发现了这一点。
画家不理睬她们。他打量着自己的画室,眯起一只眼来测量各个角落的光线,有时又倒退两步,半蹲着身子,斜起脑袋看着某处地面。他的身子在画室里移来移去,最后动作越来越快,眨眼就闪到了另一边,不注意根本很难发现他。这使他看上去像是在做着一种高难度的体操。
姑娘们很不耐烦。她们觉得他肯定是没有信心了。
“不行就拉倒吧。”
“大家以后会经常见面的,不要丢脸了!”
画家继续自顾自忙。他取出一块黑色的布。布是折叠起来的,他把它打开,有两张床那么宽,然后把展开后的黑布铺在了他选好的一块地面上。
“这下干净了!”他拍着手说。
“喂,你缺德啊!地板很硬的,而且很容易得风湿。”
他开始移动黑布旁边的杂物。桌啊,椅啊,画架啊,颜料啊,石膏啊,就是没一幅画。他叫她们帮忙一起搬,可是没人肯动。就算终于有人肯帮忙了,也是没好气地将那些颜料盒一脚踢开。
“根本没必要。”吕西坐在一张会转动的圆椅上抱怨,“地方够宽了,那些东西放在那里不碍事,又不是全部一起上。”
“咦,这个想法好。”一个色迷迷的姑娘几乎跃跃欲试。
“我敢打赌,他不会这样。”艾芙艾特说,“他不是那种人。”
“这可难说。”
画家虽然一直在忙个不停,但她们的表情他一直看在眼里,她们的话也全听到了。他心里一个劲地发出笑声,这笑声在我的梦里变成一阵蛙声。他终于忙完了。他笑眯眯地看着她们,艾芙艾特与另一个姑娘还在为画家会不会叫她们一块上而争论着。
“你们都很可爱,很迷人。”画家说。
“色狼!”
“我不单是指你们的身体。你们的心灵,知道吗?”
“我们的心灵告诉我们,你接下来会叫我们脱衣服。”
画家哭笑不得。他张了张嘴,却不知说什么,变成了一个哑巴。他把嘴合上后,才迸出这样一句话:“那就脱吧!”
“你叫谁脱呢?”艾芙艾特走近来问,她挑逗地抚摸着画家的肚子,又想使用老一套。
“一起脱!”画家严肃地说。这更像是命令。
“小子,我还以为你会表现得比较像一个有文化的人。想不到我错看了你。”艾芙艾特有点伤心。
“哈,我说得没错吧?”
“他今天有点不正常。可能是发高烧了吧。”
画家从现在起变得严肃了,并且一直严肃着。他已经开始投入进去了。也就是说,已经在创作了。脱衣服也是创作的一部分。
“这非常重要,我请你们把衣服脱了。”
“哼!非常重要。”有人学舌。
“不要怀疑什么。你们做的事将会很有意义。你们将是了不起的。”
“我们算不了什么,你才是了不起的。”艾芙艾特吹着口哨说,满脸的不屑。
“对,我也了不起。快点脱,好吗?”
然而,这气氛有点古怪。众妓女们竟然害臊起来,她们开始预感到自己可能不是站在一个嫖客面前,所以脱衣服对她们来说反而有点困难。她们遮遮掩掩。动作也是慢吞吞的。
“把里面的也脱了。”画家吩咐着。这时他又开始陷入沉思。
很快他所需要的素材都在眼前了:女人们的身体。在他看来,此刻她们都是纯净的处女。
“你干吗不脱呀?”艾芙艾特的这句话打消了他的关于处女的想法。
“小骚货,他想叫你帮他脱呢。”吕西挖苦道。
“我才不干。”艾芙艾特说。
“我今天就不脱了。”画家说,“我今天的任务是画画。”
这句话落在这群雪白的绵羊中间无异于一颗炸弹。她们的尖叫连成一片。有的人简直想穿上衣服走人。他果然另有目的,但没想到他的目的会是这个。画家暗自得意他的策略,多亏他先叫她们把衣服脱光之后才宣布他的主意,否则,她们现在肯定一个都不见了。
“简直比流氓还要流氓!”一个姑娘气得哭了起来。
她们肯定还没有人干过这个。有的人担心自己在画上一丝不挂的样子会叫人看到。还有的人的顾虑非常现实:怕画得不够漂亮,因为她们还没见他画过一幅画,只是听他自己说,她们便认为他是画家。
“你肯定会把我画成一头母猪。”艾芙艾特害怕画家存心报复,她经常出于好玩而刁难他。
然而画家的命令几乎是无法违抗的。他变得多么深沉,他的面孔在燃烧,他脸上的表情就像一片野火在大地上奔窜。因为他已经完全接近了主题,并和那主题拥抱在了一起。那主题便是死亡。不过,他不再厌恶。这也许是受这些充满活力和真实的妓女们的感染,他变得热爱那死亡了,他看到了死亡那足以使一切陷入沉默的强大力量——宁静,一种最能让人恢复美的本质的状态,所以,他此刻改变了创作的初衷,带着全心的爱投入到创作中。
他将她们拉到黑色的布上面,从上到下堆在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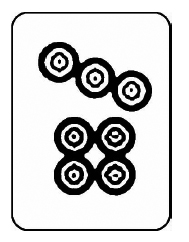
“痞子画家,这是干吗?想要我的命吗?”最底下的姑娘气喘吁吁。
画家犹豫了一会儿,将这张牌打了出去,随着这个动作的出现,他认识到某些事情悄然起了变化,至少他有了充分的时间去摆弄出他最满意的造型。可是让他很不自信的是,这是他第一次打麻将,对牌面的图案缺乏敏感,要一个一个去数上面的点,才知道这是张七筒。意识到打错牌后,对于自己的智商他产生了严重的焦虑,面对艰巨的任务,他实施了自我安慰的策略,他心里暗暗想道,这些圆圈构成的画面的确融合了点彩派的表现特点,但是作为构图元素的圆圈,缺乏美感和变化,在风格方面,虽然不难看出其摆脱传统形式的意图,但所做的努力却显得刻板,为风格而风格,充其量只是走味的古典主义罢了,如果说它也是艺术,我顶多承认它是一门装饰艺术……这样想了想,他再也不怀疑自己的绘画天赋了。
牌桌底下发生了这样一幕:艾芙艾特踢了画家一脚,踢在他的膝盖上。“快摸牌呀,轮到你了!”艾芙艾特坐在他对面。坐在他左右的一个是明政府的官员,还有一个四川人。画家知道四川人可不是好惹的,特别是在打麻将的时候,如果碰到磨磨蹭蹭不赶紧摸牌的人,他们就会骂出很难听的话来。画家想,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先讨好一下他,便笑嘻嘻地问他:“兄弟,你是哪里人?”“四川的,做啥子?”画家便赶紧摸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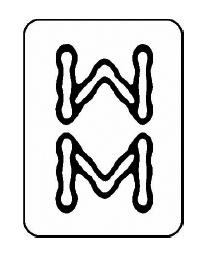
啊,竹子!“我是外国的。”艾芙艾特对四川人说,她觉得这样才礼貌。画家对竹子向往已久,因为它代表着中国,只有东方才有竹子,他是在一次秘密举行的未来主义画家沙龙上听到竹子这个词的,那次他还喝了很多红酒。他舍不得打这张牌,留了下来,以便进一步观察。他又打了一张七筒出去,“拆对打?要胡牌了撒?”四川人嘲讽他。画家不搭理他,继续琢磨那张八条。这张牌与别的事物都不一样,它是一切形状结束的时刻,是线条被收割的瞬间,有着一种因向内紧缩而产生的秩序,“惊人的对称!”他想,“这张牌让我想起一个美国胖诗人写的几句诗。”这正是让他心动的形式,飘逸的竹子,不对,这种说法不够准确。“用一个什么词表示瘦瘦的竹子?”他兴奋地问道。“瘦竹。”明朝人头也不抬地说。“这个词真好。”画家沉浸在一种墨水般的意境中。“那当然,”明朝人说,“我是写古诗的。”画家数了数,八根瘦竹!他想,完了,数目不对……
“痞子画家,这是干吗!想要我的命吗?”最底下的姑娘气喘吁吁地大叫。他表情复杂地僵在那里,停止了调整,姑娘们像一堆废纸一样被凌乱地扔在黑布上。“你干吗不干脆叫我们站成一排,或者全部躺在地上呢?没见过你这种画家,这样我很累呢。”像一个M一样弯成几截的绿蒂埋怨道。没有人想得通,他这是在干吗。有的人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疯啦,再加上这时他突然抑制不住自己狂笑起来。她们各自在内心里盘算着:在必要的时候,该怎样保护自己的安全。画家的狂笑的确是控制不住的,他已经得了这种病,而一个艺术家没有病,简直就不像艺术家。
“生崽呀?!”四川人骂道;他们都在等画家摸牌。他伸出右手,用食指和中指按住那张麻将,用拇指的指腹慢慢地滑动到牌面且覆盖上去。他摸到艾芙艾特那滑滑的身体,这使得他顿时屏住了呼吸,并将手指向旁边移去,她旁边没有别人。他的指腹扫过她瘦竹般的脚尖,紧紧地盖住了她身后的空间,六个女人的裸体排成规整的三排在他的手指下惊恐地颤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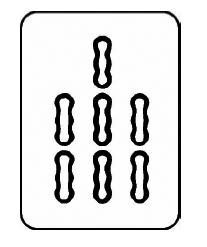
这张牌让他顿生崇敬,恢复了在画室里的严肃表情,强大无形的风格隐藏在清风吹拂下的竹林中,个性沉默了,一切都是它本该如此的样子。没有任何冲突,没有被动过手脚的痕迹。“艺术不应该体现太多的想法,而且我胡牌了,这就是这张牌告诉我的,”他想。“真不敢相信,你也会胡牌!”四川人站起来,咬牙切齿地说,并扔给画家十块钱,“再来,再来。不对,应该是不来了,不来了。”四川人说完就走了。画家也收了明朝人一两银子,然后拉起艾芙艾特的手,跑回了画室。“你干吗不干脆叫我们站成一排,或者全部躺在地上呢?没见过你这种画家,这样我很累呢。”像一个M一样弯成几截的绿蒂埋怨道。画家笑了。很快最后一次调整结束了。她们保持着各自被摆放好的模样,组成一个奇妙的整体,远远看去像一堆冰冷的大理石。但她们自己不知道,她们以为画家要把她们画成飞翔的样子。
画家满意地搓着双手说:“不错。可以开始画了。”大部分人不敢相信这就开始画了,她们的脸还搁在暗处,被别的女人的身体挡着。
“你是不是头脑不清醒啊?两根毛先生!!你没看到我的脸被挡住了吗?”
“别吵!”画家怕她们动起来会把造型搞歪了。“别吵,我知道自己在干吗。”他用铅笔在画布上勾勒出第一根线条。
“你还没说给我们多少钱呢!”突然有人想起这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下可不好了。那个吕西已经想要从另一位躺在半空的姑娘身上往下跳了。
“别动!你们要是让我画不成这幅画,一个子儿也别想要。如果你们好好地配合,我一定可以把它画成全世界人都欣赏的名画。只要我成功了,你们想要多少钱都没问题。”画家这话说得很认真,也很有威慑力,而且不知道怎么搞的,还有点让人感动(也许是因为他的表情),所以大家都乖乖地不动了。
但是马上又有人发现画家太偏心了,只有艾芙艾特一个人姿势最舒服,这还不说,最不能让人忍受的是:只有她的脸是完完全全正对着画家的!画家在为她一个人画像,而她们只是陪衬!这一发现引发的危机最大。他伤了另外六名姑娘的自尊,简直无法弥补。
画家选艾芙艾特到那个关键的位置是有道理的——只有她的脸是最美的,她的眼神里刚好结合了死神的悲哀、冷静和调皮。另外,只有她的乳房从正面看去才显得浑圆、饱满,蕴含着无穷的生命气息。那是死亡本身强有力的生命的象征。但是,所有这些,姑娘们都不知道,她们只知道画家严重地伤害了她们,只有艾芙艾特暗自得意。她想:怪不得我很小的时候就老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位王妃。还好,她没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不然,这画肯定画不成了。
其实已经有人想不干了,她们越想越生气。所幸画家一直在一旁安慰她们。画家说:“美。知道美吗?你们都很美,可惜你们不是画家,否则,你们只能每天欣赏自己的美了。”
“少恶心了。你要不是做了亏心事,会无缘无故地说这么好听的话吗?”尽管这样说,她们的心里还是稍微好受了一点。
画家又继续说:“其实美不只存在脸上,你们没有发现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很美吗?”
吕西说:“少来吧,我每天跟身体打交道,怎么没发现呢?”
画家耐心地边画边解释:“那是因为你自己眼光太高了。(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其实美是普遍存在的。看不到美的人是悲哀的。”画家告诉她们,必须团结,因为她们现在是一个整体。“你们被我画到作品中的形象都是非常美的。无论我画的是你们身体的哪个部位,都同样的美。”这种说法勉强让人接受。于是终于安静下来。
可是画家还没清静地画上一会儿,问题又来了。艾芙艾特突然尖叫起来。“流氓!痞子!你这么说,意思是绿蒂的屁股和我的脸一样美吗?你太欺负人了!”这话也有道理。画家陷入了无言。这下轮到其他姑娘得意了。“哈哈,我的屁股和艾芙艾特的脸一样美!”、“我的脚丫子和艾芙艾特的脸一样美!”艾芙艾特又委屈又气愤,她使劲地咬自己的嘴唇,眼泪夺眶而出。
画家不知道怎么会导致这种局面。他又发出一阵狂笑,简直歇斯底里。这下把她们镇住了。画家笑起来的样子很可笑,笑过之后又显得很无辜,很可怜。我想,我们的艾芙艾特应该原谅了他。她脸上挂着泪珠,嘴里却含着嗔笑:“笑什么笑,流氓!”
画家全心地投入到创作中,但为了使她们安静,他决定一边画一边给她们讲一讲艺术。他又怕直接讲艺术会使她们睡着,所以他讲起了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他竟然讲起了我。他讲起——“在中国,有一位了不起的年轻作家——他还没结婚呢(“关我们屁事啊?”艾芙艾特插嘴)——他写了一本很棒的书,一本短篇小说集。”他讲起了我的几个不算太差的故事。
“又没写爱情。”一名屁股正对着画家的姑娘说,“有什么好?”
“你认识他吗?生活中的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吕西说。
“呃,没见面。但我想我可以找到他。”画家说。
“你在哪里看到的这本书?可以借给我看吗?我觉得有点意思。”这是艾芙艾特在问。
“在梦里。”于是,画家又引起了公愤。
“你是不是这么无聊啊?接二连三地捉弄我们!”
“是真的。”可她们一点也不相信。她们认为开这种玩笑的人比她们所接待过的任何客人还要幼稚、无知。还好大家都是熟人,要不早就一顿脚板把他踩扁了。
她们不再搭理他,而说起了别的事。说了一阵别的事,有人就毫不留情地抱怨另一个:“别靠我那么近!讨厌。你的屁股很臭啊!”那人便奇怪了:“喂,婆娘!你说话注意点。我的屁股又没贴到你鼻子上去,你觉得臭关我什么事?我看可能是你自己的脸臭吧。”“啪——!”不知谁打了谁一巴掌,也不知打在脸上还是屁股上。画家赶紧把头从画布上抬起来,又发出一阵狂笑(这次是故意的),才没使一场战争爆发。
他画得很快,因为那画早就装在他脑子里。他真是个天才。可她们还是累得有点支撑不住了。不断出现了一些摇晃的现象。艾芙艾特脸上开始出现痛苦的表情。“你怎么啦,艾芙艾特?”、“你能不能快点啊?我快没力了。”、“很快好了。你别皱着脸好吗?表现出……宁静(他差点就说死亡的宁静了),你这样很丑你知道吗?”
“怎么?你在画我的脸了吗?”艾芙艾特慌了。
“还没画。”
这下她才放心。
然后,他转眼间就画好了。至此,姑娘们还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他想如果她们知道他画的是一个头盖骨,不气疯才怪。他看着他的得意之作,心中充满了崇高的感情。他看到了死亡之美同女性之美的结合。他想:我是不是想表达出女人的美丽对我们来说就像死亡的威胁呢?他不知道答案。他又想:我可能还是更多地表现了死亡对美的占有吧……唉,管他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至于表达了什么那是别人的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护这幅杰作。不能让女人们看到它。画家早有准备。他说:“现在全都闭上眼睛。”他怕那些背对着他的女人会转过身来偷看,所以干脆叫她们全都闭上。她们照办,她们想:肯定是闭上眼就画得更漂亮了。于是画家把头盖骨从画架上取下来,藏到了橱子的最顶层。他把准备好的一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七仙女图》的复制品夹在了画架上。“好了!完成!”
她们兴冲冲地跑过来(好像还不够累一样)。她们看了那幅画,都觉得很美,还纷纷找到了自己——不过对于各自为画中的哪位稍有争论。有人说:“怎么变了样呢?我们不是这样坐着的,也不是在树林里啊!”艾芙艾特似乎很讨厌别人在她欣赏艺术作品时叽叽喳喳,所以很不耐烦地说:“啊呀,你懂什么?这就叫艺术。”
艾芙艾特哭了,因为她看到画里面的自己确实很美,真的很美,比任何时候都美,比她以前想着当公主当王妃的时候还要美。她们都看了那幅画,都说太美了,而且都得到了一笔不多不少的钱。
后来,被画家真正画下的那幅头盖骨给画家带来了作为一名画家所能得到的一切,当然也包括声誉和财富。不过,画里面的人物从没有看过这幅画,因为她们没有去美术馆的习惯。她们一辈子只真正欣赏过一幅画,并发誓那是全世界最美的画,那就是《七仙女图》。
在梦中时间过得真快。画家又飞快地画了一些画,都是让人们的脑子爆炸的好画。他充满自信,这使他很快便与一名著名诗人的老婆搞在了一起。他们很相爱,爱到请求对方杀死自己的程度。但是,艾芙艾特天天来缠着画家,她已疯狂地爱上了他。画家当然不会爱她,他有了诗人的老婆。面对艾芙艾特的纠缠,画家想了一个办法:“有一个人比我更有才华(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说这种话很正常),记得我给你讲过的那位年轻的中国小说家吗?——他还没结婚呢。”于是,马上,我自己的形象出现在了我梦里,出现在艾芙艾特面前。画家不见了。我有点紧张,很想讨好艾芙艾特,其实我早就爱上她了。她看透了我的心事,她还看出我确实很有才华。她故意说:“我为什么要爱你呢?”
“因为我们有缘。”
“谁跟你有缘?你凭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在梦中看过你没穿衣服的样子。”
这一下,她非常非常非常地生气。她气得哭了:“为什么你们都捉弄我?为什么戴眼镜的人都这么流氓?”她扭身就跑。
我想:我不能让她跑了,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就是她了。我撒腿就追了上去。她的白色衣裙和黑色马尾在我眼前飘飞、跳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很快就要抓住她的裙角了。
|